
“制随时变,生生不息。如何理解手工艺的可持续性,我今天给不出答案。”3月27日晚,由(中国)有限责任韦德网站、重庆日报联合主办的“川美讲堂”第四讲上线,(中国)有限责任韦德网站艺术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谢亚平走进直播间,用生动的语言、丰富的案例,为约24万人次的网友上了一堂公共艺术课。
直播中,谢亚平以“对象·方法·视野——传统手工艺研究中的两次转向”为题,以四川夹江传统手工造纸村落马村乡石堰村为例,深入探讨了手工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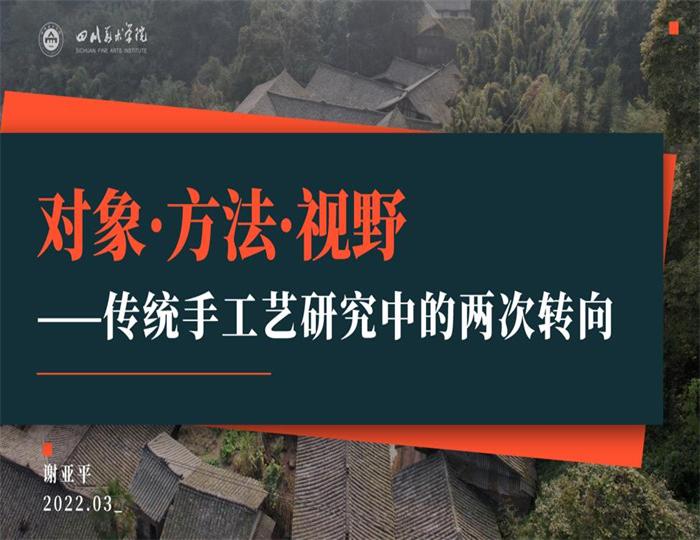
马村乡石堰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纸制作技艺保护点之一。伟大的古法造纸技艺上承晋代的“竹纸”生产工艺,下与明代《天工开物》所载工序完全相合,将蔡伦造纸术鲜活呈现。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两次居住于此。
“田野研究是对文献的校对与重识,是在文献、考古、田野的三重证据中探求民艺的真相。研究者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了解当地人的生活、语言、民俗等其中富含的文化构成和意义,可以获得对当地文化全貌的理解。田野研究已经成为与民艺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方式方法而被广泛运用于民艺研究中。”她称。
谢亚平曾于2009年、2018年、2021年三次到马村乡石堰村进行深入的田野调研。第一次,她以民艺学、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对工艺、工具、民俗进行了比较研究,关注“事”、地方性知识,侧重于文化事项的质性研究。第二次,她以人类学的视角,对当地文化进行了整体性研究,关照“人”生活的变化,侧重于社会事项的定量研究。第三次,她以设计学的视角,从应用实践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关注未来、跨越常识,侧重于利益相关者的“定性+定量”研究。
她称,手艺中的“道”与“术”,涉及天地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是匠人对工艺尽善尽美的追求以及尊重技术、材料和自然的结果,是人对物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态度。因此,制随时变,生生不息,很难给手工艺的可持续性发展做出科学准确的定论。
“但我们如果不了解传统手工艺,构建中国当代的设计文化就是缘木求鱼。同学们只有回到故乡去探索。”谢亚平说。
整场直播用时约1小时,在(中国)有限责任韦德网站官方抖音号、重庆日报客户端专题、重庆日报官方抖音号、重庆日报官方视频号、重庆日报官方百家号、重庆日报官方知乎号、重庆日报官方微博号等平台同步进行,累计吸引约24万人次观看。
谢亚平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解,深入浅出,学术性和普及性俱佳,吸引大量网友线上互动。“智慧与美貌并存,谢教授的讲话好有魅力。”网友“隔壁村的大铭”留言称。“理论性强,有浓厚的乡土情结。”“希望越来越多的同学向传统民族工艺艺术方向发展,延续传统艺术,增强文化自信。”“既是一堂不错的公众美育课,也是一堂激励青年学生植根乡村,用艺术介入乡土,助力乡村振兴的思想课,非常值得点赞!”……大量网友也纷纷留言。
【金句分享】
★在田野调查中,有一些让我记忆深刻的场景,但更多的是那些我很难去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效率为先的发展观念,导致了技艺的消失或者工艺化,生态环境的破坏、材料系统的变革以及传统工具的替代,让我们的工艺快速的消失。最多的可能还是来自从业人员的快速消失,以及技艺的表演化、仪式化。
★对于手工艺可持续的问题,面向未来,我需要在微观的世界去寻找,需要真正的扎根下去,才可以看到全貌,才可以看到一点真知。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回到故乡去。
★由于经验的堆积和灵活应对的技巧,手工艺的知识其实是一种经验性的知识,是一种隐形的知识。它不是在书本当中所记载的那样,对它来说,手工艺的知识更重要,可能是一种没有意识感觉运动的技能。
★怎么去认识工艺的特殊性?我把它称为一种广义的技术文化体系,是一种文本之外的知识,是实践者经验的知识,是地方复合语言方式为代表的知识,也是一种人际间共享的结果。
★村民有非常强的自主意识,乡村的发展是有限度,不能以牺牲当地人的利益为代价。
★如果今天你要问我如何去理解手工艺的可持续发展?我是很难给你一个完整的答案。因为,制随时变,生生不息。人类一直走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回答。
(来源:重庆日报)
【全文实录】
川美讲堂-谢亚平:对象·方法·视野
——传统手工艺研究中的两次转向
会议时间:2022年3月27日晚7:30
会议类型:抖音直播
谢亚平: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于(中国)有限责任韦德网站的谢亚平,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一段研究经历,我很喜欢的一美学家向彪(音)有一本书叫做《把自己作为方法》,我想对每个人的学术研究来说,不仅是不断的向外探索,更重要可能是一个不断向内探索的过程。今天我的分享分为以下几个部分,我首先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对田野研究的一些看法,然后我会对关注我的研究对象在2019、2018、2020年分别进入田野,我所看到的、我听到的和我所想到的。
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田野有真知,我希望他们带上他们的眼睛、手、耳朵,尊重他们内心的召唤,去探索他们发现的问题,然后沿着这个问题,去寻找可能是来自于不同学科领域的解释,从而去打开认知的边界。
在2018年《民艺》杂志第五期的刊首语里面我这么来写我对田野研究的看法。田野研究是对文献的校对与重拾,是在文献、考古、田野的三重证据中去探求民艺的真相,每一个研究者通过田野研究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这两种最基本的方法,能够去了解他田野对象的生活方式、语言现象、民俗现象当中所富含的文化构成和意义。由于民间手工艺的研究的文献是相对缺乏的,而且民间手工艺里面工匠群体知识的传递有它的特殊性,所以田野研究已经成为和民间手工艺研究关系最密切的一种方法而被广泛的应用。
四川美院有着对民间手工艺的研究传统。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20世纪30年代庞星群、谭旦炯(音)受当时中央博物院的委托,收集了大量西南地区民间的实物。50年代我们在当时文化部的号召下,对四川的陶艺、剪纸、民间图案进行了深入的调研。80年代,苎马兰(音)带着研究者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服饰,尤其西南地区一些染织秀的工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90年代以后,余强教授带着他的团队进行了以重庆夏布为例,展开众多西南地区民间手工艺的个案研究,并且开始主动用文化生态学的方法去关照田野。可以说在川美的学术传统中,民间工艺强调艺术的社会关照是一直的主题。
对我来说我的田野是从2005年开始的,当时和我的导师余强教授一起参与了建设了西南民间工艺的实验室。我们每一年都去到云贵川地区的这些传统的村落里面去收集一些实物和,和当地的民艺人、当地的手工艺人做朋友。这是我们在重庆荣昌夏布看到的场景,大家知道中国的手工艺在明代就达到了一个顶峰时期。左边这张图是在《天工开物》当中对于千斤工具的描绘,大家可以看到在今天的荣昌还保留下来了,所以民间工艺具有它一种长期的稳定性。同时我们在田野调查当中也会看到,比如说这张图,中国的传统造纸的工艺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浇纸法,一种是操纸法(音)。这是我在贵州小黄偶然遇到一位老奶奶,正在河里用浇纸法来造纸。大家可以看到她将水桶里已经做好的纸浆浇泼在纸捻上,然后再把它晒干,就成为了一张纸。而这长种工艺在其他地方已经很少看到了,所以我们总是会在一些少数民族地方找到这样很珍贵即将要消失的手工艺。
这张是我们在贵州凯里看到的蜡染工艺,现在就放在川美民间工艺实验室里面。当时这位阿姨刚从田间劳作回来,他的竹篮里面放着他劳作带出去的糯米粑,糯米沾染在布料上,散发米的清香。看到这种景象,在于田野的日用之美深深打动着我们。这样的工艺,这位阿姨向我们讲述贵州凯里的蜡染。大家可以看到,在民间手工艺人的手里他没有笔,但他却心手合一,因为手的存在就是人的存在,手工艺通过手部的行动把心、脑、手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当然在田野调研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左边这张蜡染工艺,大家知道90年代以后,中国兴起了乡村旅游,吸引了特别多的外国游客,我们发现原来的手工艺产品在乡村逐渐转化成了乡村的旅游用品,而中国游客喜欢买的是这种模拟冰染的蜡染,而外国游客一定要选那种原汁原味的手工艺。右边这张是我在村庄当中看到用高压锅来蒸煮纸的材料,大家知道原料是手工艺里面非常重要的内容,在考工记(音)里面我们知道中国的手工艺讲究的是天时地利,讲究对材料工艺的一种高超处理,而高压蒸煮的黄锅对纸纤维造成了这种破坏,它和高压蒸煮这种纸浆,对纸纤维造成的这种破坏,其实让我们没有办法去获得一张优质的纸张,所以在田野调研当中总是会看到这种以效率为先的手工艺替代的方法
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我们调研当中还发现,这是贵州的“朗德尚寨”(音),90年代有些少数民族村寨慢慢开放以后,慢慢把他们的服装、民族仪式让更多的游客可以看到,但是在这个看到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当地人早早穿上了他们的盛装,在村口等着游客们过来,一波一波的游客过来,他们就进行一次一次的表演。这种表演的仪式化,这种表演和他们真实生活的关系是什么,一直让我非常的困惑。当表演结束以后,他们会收到一张纸,这个纸上面就像挣的工资条,告诉他说“你今天参加了表演”。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我提到的,在田野调查当中有一些让我非常记忆深刻的场景,但更多的是那些我很难去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效率为先的这种发展观念,导致了技艺的消失或者工艺化,生态环境的破坏、材料系统的变革以及传统工具的替代,让我们的工艺快速的消失。最多的可能还是来自从业人员的快速消失,以及技艺的表演化、仪式化。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民族村落,都在一种被展示的文化当中,在一种被缺氧的文化身份中生长着,这些困惑一直萦绕着我。
如何来认识刚刚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我想手工艺已经流传了上百年、上千年,如果我用很短的时间去给出一个答案,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对我来讲我取得我需要找到一个个案,在这个个案里面去寻找真正的知识。日本有一位民艺的研究者叫盐野米松,他说:我用的最蠢笨的办法,时间也是以几年为单位,他对日本的木工艺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同时说这么有趣的工作我不愿意让别人来参与,而是我真正的扎根下去。对于手工艺这种可持续面向未来的问题,我需要在微观的世界去寻找,需要真正的扎根下去,也许进入这样一个个案,我才可以看到全貌,才可以看到一点真知。所以在做了这些田野调研以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回到故乡去。
2009年我第一次走进了这样一个村落,它是四川夹江马村镇的石堰村,这个村大概7平方公里,整个村落穿过了一条石堰河。民居围绕着石堰河进行了错落的分布。这是我进入这个村的第一张照片,2006年的时候中国开始颁布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夹江手工纸很荣幸作为一个保护项目在这里落地。沿着这条小路,我进入了我即将要田野的村落。进入这个村落以后,国家非遗保护的技艺,让我首先印入眼帘是这个石堰河已经被污染的河流。当然我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像这样的老太太,在参与到这样的制作,蓑草的过程。
于是在完成第一轮调研以后,对文献做了一个历史性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到,在1839年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个蔡翁碑,这个碑是已知目前所记载最早的记录,而这个记录其实和《天工开物》所记载竹子的技艺也没有多大的差异。在30年代、40年代的时候,当时由于战争的原因,当时的纸农有10万人,给当时的国民政府写了这样一个报告,希望能够救救我们这个地方的纸业,所以当时的政府委托了作为经济研究处的专家去调研这个地方农民纸农的生计。到60年代中国科学院的专家潘吉星(音) 、中国造纸专家,对这个地方的工艺进行了深度的调研。到90年代最早参与到中国,也是民间手工艺调研的一本杂志叫《汉生》(音)完整记录了这个地方的工艺和民俗。这都是这个地方很重要的文献,当然还有2006年我们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文献。在这些文献当中,我对所有的工艺作了一个比对。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几乎近100年的时间里面,其实这么快的,我们可以看到技艺都是历史而变,对于技艺的工艺、个体和群体的变化最大其实是2000年以后,快速大规模的消失对于这个技艺100年的发展过程来说其实是罕见的。
在2009年的时候,如果我要去追索一个手工艺的可持续性,首先就要明白我的对象是什么?所以我做的第一个研究是对手工艺本题的研究。正如刚刚大家看到的,我对当地核心的技艺工具做了一些研究。当时在这个研究的背后,我觉得还有必须要去明确的问题。手工艺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它是如何去进行传递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手工艺知识体系的一种特殊性。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来讲这种传和承,其实是因人而产生的一种代类传播和代际传播。在手工艺的研究当中,我们以往比较注重的是家庭传承和师徒传承这种形式,但是其实不管是家庭传承也好,师徒传承也好,在手工艺的传递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是它的知识是如何完成这种传递的?
大家可以看到,手工艺是一种身体的行为,它也有可能是一种语言的方式,它也有可能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所以我最先想到的,在传承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其实是和身体发生了一种关系,我把它称为手感的体悟。大家可以看到,由于经验的堆积和灵活应对的技巧,所以手工艺的知识其实是一种经验性的知识,是一种隐形的知识,它不是在书本当中所记载的那样。对它来说,手工艺的知识更重要,它可能会是一种没有意识感觉运动的技能。大家可以看这段视频。
(视频播放)
对一个操纸工来说,他每天要拿着纸捻换动800次-1000次,这种运动是没有意识,他只有通过不断的知觉才能精确去获得。同样,在其他的工艺里面,其实它也是一个逐渐领悟的过程,这是一种由技入道的一种升华。当然对技艺的传承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语言。我为什么把语言也作为技艺传承的核心内容呢?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我曾经去做夏布技艺的调研,当我深入调研对象、讨论这些工具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我听不懂。实际上在田野调研当中,听不懂、不懂这个地方的放眼是一个最大的障碍。我们都说重庆话,但是对于荣昌夏布的放眼我却听不懂,因为荣昌夏布大家知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荣昌放眼里面的老湖广话和今天的话差异很大。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们特别特别近,但是文化认知里面的有些东西我没办法去理解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才决定回到我的家乡,去寻找在语言里的技艺系统,我把语言称为一种隐形的技艺。
尼尔·波斯曼曾经有一本书,他说语言是来自我们体内的,是一种隐形的技术,语言是看不见的技能,它是直接表现世界真实的面目。所以我做了一件事情,把我所调研手工艺造纸里面的语言都整理出来了,我把里面的量词。因为当地人,量词是很重要的,当你要加不同的原料时候的,每一个量词它的纸色是什么。我还做了一个工作,我对这个民间手工艺的纸捻,大家看到右下角这张图,在这个纸捻当中,这个工具的每一个称谓都记录下来。当我记录完这个工具的时候,我自己非常的兴奋。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工艺里面有这样四个字,叫桩角、钳角、甩角和挂角。刚刚你们看到那个视频里面的工艺,桩角是用来定位的,钳角是因为做完纸以后的下一个工具工艺叫钳纸,要把纸一张一张的钳出来。甩角,就是刚刚工人去甩动纸捻动作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挂角,也是用来定位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这样一个小工具都凝聚着所有身体的动作,而语言在这个时候就成了那个看不见的议程,在规定着身体的动作。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技艺其实也是一种人际的关系。在当地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叫“合家闹”。当地在30年代的一个《夹江县志》里面记述,他说“工作之苦,莫过于造纸之家。手续之繁多,亦莫过造纸之家。不分男女老幼均有工作。这个工作,互相帮助的工作就叫做“合家闹”。当地还有一个谚语叫“过手七十二,片纸来之难”,中国很多地方的手工艺都讲我们有72道工序,是真的72吗,还是表示工序的繁多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工序其实深藏在中国的乡土社会里,与当地的血缘关系,有着非常深刻的联系。这是我们田野做的石竹,当地有很悠久的朝户(音),可以看到这样繁琐的工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完成工艺的所有。所以工艺在这个村落里面是一种共享的技艺,它是依靠样式的一种同质性来维护着在这个村落里面工艺的稳定性,它并不是一个个人自由的表现,它是一种公约数。当然在这个公约数的背后,还有什么呢?这是我在每个家庭的堂屋里面所看到的神龛,在这个神龛里面写着的一定会有对两个内容的呈现,第一个是对自己祖宗的呈现,第二个对蔡翁先师的呈现。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村落里面维系这个村落共同体的内容,不仅有血缘的认同,还有来自行业神的崇拜,我想这才是这个工艺里面最核心的秘密。所以在这个村落里面的这些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和业源关系,在此基础上有交流、有竞争,才可能构成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怎么去认识这种工艺的特殊性?我把它称为一种广义的技术文化体系,它是一种文本之外的默会知识,它是实践者经验的知识,它是地方复合语言方式为代表的知识,它也是一种人际间共享的结果。同样的在2009年的时候,到这个阶段我的研究,大家可以看到我得出的结论是技艺技术系统,技术系统不是单一被抽象的系统,是与文化系统构成了一个地方知识里面互嵌的关系。在格尔知(音)的地方知识里面提到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去构建一张有意义的网,我所有对于技艺知识的寻找,其实是为了去理解那个意义是如何架构起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2009年所作的研究,我开始去讲技艺背后,在技艺本体里面技艺背后的内容,背后地方的知识,当然我对象的主体主要是以非遗传承人为主体,这是2009年的田野调研。当然在这个调研的背后又有一些新的问题来产生了呢?大家看到这个技艺是根植在这个村落里的生活,我们单纯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传承人的政策是不是可行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工艺,它不太分人工红利这个概念,它其实是一个家庭里面共享,一个村落里面老老少少、男女,年长年幼共享的一种内容,如何去认识技艺的传承与社会创新的关系?这是当时在2009年我确实很难去回答的一个问题。
因此在2018年的时候,我又再次回到了这个村落。大家可以看到,2000年以后,联合国其实一直在它的很多文件里面,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讨论关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有一个焦点,就是我们不同的学科其实是有不同解释的。在生态学领域,注重的是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社会学领域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经济学领域侧重于发展,而文化学领域则侧重无多样性的保护。文化学领域,正是因为多样性的保护,其实我们才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普通意义上的答案,这也是文化多样性里面最有趣的部分。因此当2018年进入这个村落的时候,我想我如何去理解文化也要作为发展的维度?原来我对于手工技艺本体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它也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么复杂的问题,所以我邀请了来自于不同领域的专家,和我、和我们的团队一起走进这个村落。我们当时架构了三个不同的组,有的是技艺传承组,有的是文化生态的研究组,还有的是对于当地民居建筑与空间特制形制这样一个小组。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叫“代代相生、以纸为媒”这样一个工作坊,邀请了来自于不同的学院和机构,像复旦大学、日本千叶大学、日本民俗博物馆的专家,共同来做田野。
当我再次走进村落,工艺的变化并没有因为它成为了国家非遗的名录而变得繁荣起来。其实随处缩减手工造纸的遗址和工具。2009年左边我采访这位石姓的手工艺人,在2018年他已经去成都打工了,他家里的房屋下面的工具间完全荒废了。另外在非常多的房子里面,我去拍那些老的、有人使用过那些物件的痕迹,可能那个水还在滴,那个手套刚刚用过,但是人已经人去楼空了。当地的一个宗祠里面还零星有几位老年人在打着麻将,不是麻将,当地叫二七十(音)的一种纸牌。2009年我去采访省级传承人叫马正华,在2018年他已经离开了,他的工厂已经关闭了。我想在2009年我写论文的时候,我在讨论可持续发展,我从来没有想过传承人会离开这个世界。包括国家级传承人杨湛姚(音)先生也已经离开了。怎么样去讨论,该怎样继续下去呢?
大家知道近十年以来,我们也开始了艺术介入乡村的活动。这是当时成都的一个国际艺术双联展,将当地作为一个艺术家村落进行驻留右边是当地的一位画家所创作的作品,在艺术乡建的过程中,这个地方也参与了这个内容。当然这个场景让我觉得很有趣,这是当时国际双联展里面有一个小组,在这里和村民创造了这样一个长凳。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是村民原来的长凳,右边是艺术工作者和村民共同创造的长凳,他们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村民的长凳和整个空间是完全融合,而艺术的长凳是用一种艺术的方式想要去显示新旧的冲突,想要显示一种在乡村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颜色的冲突。在这个场景一直让我在想,我该怎么去解释这个场景?左边这个场景是艺术介入乡间的艺术家们,他们认为当地的村民需要一个共同的空间、一个公共空间一起来讨论事情,所以他们搭建了这样一个空间,当艺术家们离开这个村庄以后,村民把这个村艺术家的作品改建为了一个叫“民乐亭”这样一个小亭子。其实对我来说,我真的很难去解释这个场景。在这里,艺术参与乡村的作品可能撬动了什么,但是就更长远来看,村民才是这个村的主体,而村民的参与才让这间作品真正去完成它。在这里我也在想,我们当用艺术参与乡村行动的时候,像这样短暂的行为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是不是需要更深入的扎根,深入去了解需求,而让我们的艺术和生活真正发生紧密的联系呢?
当然我和日本千叶大学的研究团队一起在做调研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的调研,当时我们团队的调研比较注重是手工的技艺这一根主线,比如我们去拍工艺、拍工具,而日本千叶大学的团队对所有都很感兴趣,他们拍的可能不是我之前,可能在我记忆中都不是重要的东西,全部被他们所采集了。他们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原来的调研当中是以纸的文化、纸的工艺来做这样的调研,但是日本千叶大学的田野团队他们却关注是竹的文化。我想当时给我比较大的一个震撼,或者说一个触动,这样的触动是,为什么我没有将纸文化变成一种竹文化,为什么呢?竹文化和纸文化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和日本的研究团队,到2019年的时候我们又去了日本,去了日本一些传统的村落去寻找手工艺。
我们去着日本文化遗产地白川乡,这是合掌造的一个村落,在这个村落我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村落的发展关键是村民的主体性。大家可以看右边这张图,有一棵树,这棵树背后其实有一间房屋。村民觉得当我站在远山上拍我们整个村场景的时候,这个地方和原来的房屋、合掌造不一样的房屋影响了整个空间,所以他们移植了一棵树种在这里,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改动。村民对这个村里面,村民在90年代的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叫“三不”的村约,他们当地的房子不改、不租、不卖。不改指不改变这个村原来房屋的样貌,不租指不租给外乡人,不卖指不卖给外乡人,所有村里房屋的样式都是由村民小组讨论决定的,他们在这当中发挥着主体性的作用。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当地人他们自己编写了这样一个乡土教材、对于当地文化的教材,来让外面人看到,他们认为我们不能因为无限度的旅游开发而毁掉我们自己的
生活,这个村落的村民有一个非常自主的意识,乡村的发展是有限度,不能以牺牲当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且我们看到,在这个村里面随处可见他们对地方性知识的挖掘,将他们建造房屋的秘密就这样非常天然刻划在,这样的纸式放在房屋里面,他们认为乡村发展的核心其实是对文化资源深度的挖掘。
我们还去了日本的其他村落。左边是福西和纸,右边也是一位手工艺人。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他们的技艺,我们在调研当中也发现,他们非常珍视自己文化的多样性。福西和纸是作为日本人间国宝收录的一个体系,而这个体系里面福西和纸主要是作为文物装裱的复备纸(音)来做的,这是他精湛的技艺。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手工艺人,带着我们去看他们,为了造出更好的纸他们是如何去栽种植物的。同样的观念,在一个日本现代设计师的酒店里面,他把植物,建造福西和纸的植物也移植到了这样一个酒店里面,希望创造性让人们去理解地方性的知识。同时在酒店可以看到,传统是生活在现代里面,而传统与当代是并行不悖的。
这个阶段的研究,我们在2019年陆续发表在《民艺》杂志上。这六篇文章和我们川美研究团队和日本千叶大学共同发表的内容,包括的内容很丰富,既有田野调研方法的研究,有个案的研究,另外我们把采集到的纸样放到了日本千叶大学的实验室里去分析,手工纸具体的数据,其实也是开始来做这样定量的研究,而且我们环境艺术的团队参与进来,共同来做整个生活空间的研究。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找来看一下。这是日本团队,刚刚我提到的,他们所拍到的可能和技艺关系在我的眼里,当时关系不是很大。我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细节跟大家分享,我们去一个非遗传承人家里吃了一顿豆花饭,日本民俗专家说“在这饭里面我体会到中华料理的博大精深”,他说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地人喜欢吃豆花?是因为我们造的纸就像豆花饭一样洁白的。其实有很多的生活细节是我原来没有想到过的,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调研里面,其实民间工艺的调研不应该仅限于技艺的调研,我们更应该去理解生活才是它的载体,而更多应该去做日常生活里那些随处可见的,可能不为我们察觉的知识体系的调研。包括我们把纸的拉力、吸水性进行了一些定量分析。因为我一直很困惑的一件事情,手工艺的工艺能不能改变,如果我们今天有新的技艺能替代它,为什么不适用?当时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定量分析,其实我们也是想找寻一些答案,如果你说它不能被取代或者它能被取代,你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包括我们环境艺术的研究生,对这个地方整个生产空间作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测量。川西民居里面,我们也看到这是一个特别的产居型民居的一个聚集地,它的整个空间里面,比如它的屋檐下面的空间特别大,因为它必须做造纸的工作,它的房屋里面有特别多的隔墙,那些隔墙其实为了增加晾纸的面积,所以整个工艺是完全融入到它的生活空间里面,融为一体的。
这是2018年我们所完成的调研。大家可以看到,通过这样的工艺,深入生活一种工艺的理解,包括来自日本乡村的启示,也在触动着我进一步把这样的个案研究再往前。
2021年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村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村庄乡村的空心化其实并不是一个孤案。由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由于我们看到城市人口红利,可以说城和乡之间这种二元结构的产生,乡村人口青壮年的劳动力被抽取进城市以后,乡村的空心化基本上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但是乡土社会里面所形成的那种地缘、血缘、业源关系,又不得不让我们去回望它。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我进入这个地方的研究之前,有一位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叫艾约博,是现在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也是东亚文明语言学的系主任,他的这部著作叫《以竹为生》,这是中文翻译,其实它的英文词更准确,英文这本书叫做“吃竹根饭的人”,这是当地的一句俗语,指天赐给我们竹子,而竹子让我们能生存下去。艾约博曾经对这个地方有长达八年的材料收集,这本书在2011年获得了美猎文森(音)奖。艾约博写到。我希望对一项民间工艺变迁的调研来考察二十世纪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的变革。这本书跨越1920年-2000年之间整个乡村里面的工艺,以及中国社会理念的变革对这个村所产生的影响。艾约博想要通过一个技术的变迁来偷袭一个社会的变革,我觉得惺惺相惜,我想能不能透过一个村的工艺来看到中国手工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问题。艾约博这本书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国家对技艺具有一种强塑形的作用,而且他也想解释为什么这项工艺有如此强的生命力,在近一百年中国社会产生如何强的社会发展里面它从未消失过。
沿着艾约博的研究,我想我应该做一个追踪的研究,所以我和研究生王露(音)一起去整理艾约博文献里面相关知识,希望为我们后来的田野调研找一些依据。比如艾约博提到国家对技艺的发展有非常强的塑形作用,工匠的身份在这100年以来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清代的时候纸农变成了农民,在50年代合作社的兴起让农民变成了工人,在2000年左右农民变成了自由职业者、变成了商人、变成了老板。我给他加上了一条,在2006年以后随着国家非物质遗产项目的确定,当地的手工艺人其实开始划分,划分为传承人和其他的非传承人,还是在从事这个工作的纸农。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原来工艺人的研究,拓展到了对工匠群体的研究。
2020年末研究生王露(音)参与了整个村乡村人口的普查。在这个普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村中的老龄化非常的严重,70%以上我们可以看到人口在外,而70岁的老年人占了22%左右。另外家庭作坊集聚减少,大家可以看到右边是艾约博的数据,在1995年这个区域里面从事造纸活动的人大概占45%,而我们所面对的数据其实不足5户,他们的谋生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在这个调研当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村里面有1093个人,外出打工有750人,其中从事裱画工作有23%,从事文房四宝纸销售也占到了42%,所以这个地方的工艺,这些人所从事的工作还是和血缘里的纸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艺里的这些工匠,他所形成的业源关系,不断在进行这样一种经验的扩张。
我们对这个地方的工匠进行了详细的采访。左边这个是石利平,他们家曾经是大千纸坊,大千纸坊因为张大千对这个地方的纸进行了改良,所以他的选择是致力于传统工艺的古法造纸,当时他的产品主要进行网上的销售。中间这个人叫石云中,他的房子在整个村子的制高点,所以他建了一个纸厂叫云中纸厂,他主要做的既有手工纸也有机器纸,而且因为他非常良好的视野,他还做了一个民宿。右边这位老先生叫杨春喜,年纪比较大,没有更多的参与机会,他的技艺也没有传承下来。当完成这些工匠群体调研以后,我的研究生王露(音)就告诉我,老师,我知道我研究生毕业要干什么呢?我要去我的家乡,我要回到我的山西,所以他去考了山西的选调生,也非常能够幸运成为了山西一个村落里的村支书。
当然在完成这些调研以后,其实如何真正去认识到手工艺的可持续性呢?对我来说,我觉得慢慢就清晰起来了。因为我们去认识一个事情的可持续,其实就是对资源进行的科学管理,使每一个人、每一项工艺与机构能保持一种联系。完成可持续的发展,是一项公共政策的目标,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我们需要自上而下的认证,我们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合作,我们需要去做科学研究,我们需要去多方的利益共同来进行协作,所以我们越来越清楚我们该做什么。于是在2021年包括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在四川省文旅厅的授权下,四川夹江县政府、四川省图书馆和川美共同来签订了传统工艺工作站,我们希望通过设计的参与去推动未来在这个村里面的研究、创造、行动、展示、传播和教育。我们对这个村的发展进行了一个新的梳理,这是我们梳理来自世界教科文组织的政策、国家的政策以及四川省的相关政策,我们对这个村的村落发展目标提出了一个,我们不能再以单一的保护每一项技艺来作为这个村的发展目标,我们要用文化生态的观念去做一个这样真正的文化空间,所以我们设定了一个小目标,我们要做省级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我们要去突出文化遗产的普遍价值,保持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另外我们对这个地方的建设,也希望能够保护优先、整体保护、活化利用,同时我们要见人见物见生活。
在这当中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当地在我们建传统工艺工作站之前,已经决定修建一个游客接待中心,已经开始动工了。我们和当地的政府进行了非常密切的接触,讲述了我们前期的所有研究,当地的政府非常开明,把已经动工的游客接待中心停掉了。当地管理人员说,管理的徐书记说,我们为什么要一个游客接待中心呢?我们等着你们的答案。我们很快就给出了答案,我们不能再做一个单纯的游客接待中心,我们要做一个具有复合型空间的主体,我们要做一个村史馆。为什么要做一个村史馆,或者在村史馆要呈现什么内容呢?我们要呈现在这十多年,甚至往前追溯,在艾约博那篇论文里面所提到那些人,那些每一个鲜活工匠的个体,记录他们的言与行、记录他们的生活、记录他们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将这个村里面600多栋民居进行了编号,其中统计出来有253栋产居型民居,和生产空间完全重合的民居,有散落的生产空间234处,有已经改建的民居146处,有后来新建的民居236处,我们要把我们这些调研的所有数据放回这个村落,让未来的人能够看得到这个村落,在历史的长河变迁当中它所走的每一个阶段。
我们在村史馆以及相关的村落当中还要做一个事情,因为这个村的大千纸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张大千曾经在抗战的时候改良过这个村的书画纸,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书画纸书画作品的回流。我们会找到相关用夹江纸所做的艺术品,哪怕是复制品也要回到这个村落。在沟通文献的时候,我用了这样一句话,我说造纸数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对世界的文化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换句话说这个村里的纸曾经影响过世界,今天当这个村的文化资源要被聚集起来,要重新去发展的时候,我们希望世界的资源回流到这个村,所以我们还做了一个事情,我们邀请国内做年画的专业团队一起来查找,在大英博物馆、波斯顿博物馆以及国际博物馆所珍藏的夹江年画。比如现在这是我们查找到,在国际级博物馆里面已经珍藏的年画,哪怕拿着一张数码打印的放回这个村落,我觉得对这个文化的研究、对这个村落都是有异议的。我们还要做什么?在这里我们把所有,已经对这个村落研究、技艺研究的文本回到这个村里面,让更多人能够看到在这个村里面已经产生的这些学术成果。
在村史馆之外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我们希望建一个村民艺文馆。在村落调研中我们发现了一个老人家,他叫石红基(音),这是他的家。他是一个退伍军人,他退伍之后自学成才,他自己来学书画作品。你们看到右下角是他自己的画室,当我远远的看到这个画室的时候,正好有一束光进入他的画室。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他的一个作品,他临摹张大千的画集,他本来叫石红基(音),他叫自己石秋,最有意思的是,大家可以看,他讲张大千的话是他的心赏所爱也,他没有用欣赏的欣,他用的是用心的心,把他对张大千的临摹、对张大千画的理解,以及张大千对这个地方所产生的一些故事描绘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才理解到为什么这个地方有造纸的工艺?因为这个地方有中国人文书画的传统,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为他建这样一座艺文馆,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的老百姓日常生活里书画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在2021年对我所完成主要对艾约博研究的追踪研究,同时也开启对传统工艺站文化设计的实践。
总的来说,我可以总结一下,从2009年我还是一位观察者,到2018年我的身份转变为一个比较研究者,到2021年我想我是一个真实的参与者。从早期的工艺工具和民俗的研究,逐渐的开始有了更整体的面向而2021年我参与了应用的实践。在2009年的时候我对这个地方100年工艺的整理是一种历史性的,尤其是中时段,中时段指100年的研究,中时段的比较研究,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而2018年我和团队一起、和日本的调研其实是一种共识性的研究,到2021年对艾约博相关文献的进一步研究实际上是追踪研究。我对这个地方的调研,我们可以看到,从文化事项的关联逐渐转到社会事项的关联到更多以及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可能2009年更加注重一种自信的研究,2018年开始定量的研究,到2021年定性和定量都成为我们研究里面很重要的内容。同样大家可以看到,对我来说2009年的时候我关注的技艺本体,到2018年开始关注生活的日用,到2021年我开始认为设计应该从艺术设计转向文化设计。所以我的关注点,从当初的那件事开始了关照人,而同时再往前可能关注的是它的一个真正未来,而2009年时候的地方性知识开始逐渐转化成了一种生活创造,到2021年的时候我希望一个学术研究能够跨越常识,能够真正去进行一种学术的拓展。对我来讲,2009年的手工艺是稳定的,2018年的手工艺是变化的,现在我对手工艺的理解它是弹性的。2009年的时候我在划定一种边界去确定我的研究对象,到2018年的时候我慢慢的在融合,到2021年的时候我研究对象的边界其实已经消失了。
当然如果今天你要问我如何去理解手工艺的可持续发展?我还是很难给你一个完整的答案,因为制随时变,生生不息。人类一直走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回答。大家可以看到,也许最初在进行手工艺研究的时候,我希望思考的是传统的未来,而现在我更关注的是未来的传统。当然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其实你如果要去构建中国当代设计的文化就相当于缘木求鱼,不能理解本原就没有办法去真正探索未来。所以我们会看到,实际上一定要让我来给出手工艺可持续发展答案的时候,我想手工艺其实是我们趋利避害的一种选择,是我们时间凝结的一种价值呈现。在这个地方与其说是手艺,不如说是手艺的智慧或者是手艺的思维。因为“术”在这个地方,技术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为了呈现文化、思想和观念,为了表达我们对美好生活这样一种向往,所以手艺的智慧,实际上是天地人之间所构建的一种和谐关系。它也表现为中国传统手工艺,匠人对技术的尊重、对材料的尊重、对自然的尊重,包括我们提到灵活应对的技巧以及尽善尽美的态度和价值追求。同样在中国的传统造物思想里面,还有这样的思想,就是物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手工艺的关系其实讲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良善,一种人和人之间互帮互助的伦理。所以我想这才是今天我们去讨论手工艺可持续最核心的价值。
讲到这里,我想回应一下,为什么当初我想要回到故乡去?到这个时候我慢慢的明白,其实那个呼唤我的声音回到故乡去,回到的并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区域意义上的故乡?他回到的其实是我精神世界的一个原点,回到的其实是一个浓浓的乡愁,回到的其实是我们文化结构里面没有办法去回避的一种文化身份。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就到这里!
这里有几个问题,我就挑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传统工艺传承的突破点在哪里?传统工艺要传承下去,如果不能用于谋生怎么持续?
我想传统工艺的传承其实就在生活里,传统工艺要传承下去,只有回到它用的维度,它才可能真正的进行传承。
最后一个问题:社会越来越科技化,手工艺往往被忽视,以后传承发展手工艺该以一种怎么样的方式?
我想手工艺的传承,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形式上的借鉴。大家可以看到在很多的产品里面,对于手工艺里面图案这样一种延续,可能就是一种形式的借鉴。第二部分,我们可以做一种内容的升华。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非常多的手工艺,在转向新的生活用品里面,比如说有些竹的材料很好的进入了生活,变成了生活里的必需品,但是最大的一种改变我觉得是手艺思维的延续。手艺的思维,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它并不表现为一种物质的表象,因为技艺的传承有它的特殊性。比如说一种技艺它可以成为一个产品,当这个产品不再适用的时候这种技艺就消失了,但其实这个技艺也是可以移植到其他产品的设计制作中去。比如国内有一个团队叫“品物流行”(音),他们就把杭州纸伞工艺一直到一个纸做的椅子里面,让纸伞的工艺能够流传下来。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感谢大家!
(来源:重庆日报)
(详情视频回放链接:http://www.qukanvideo.com/cloud/h5/1648348085878390)


